再看《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 Published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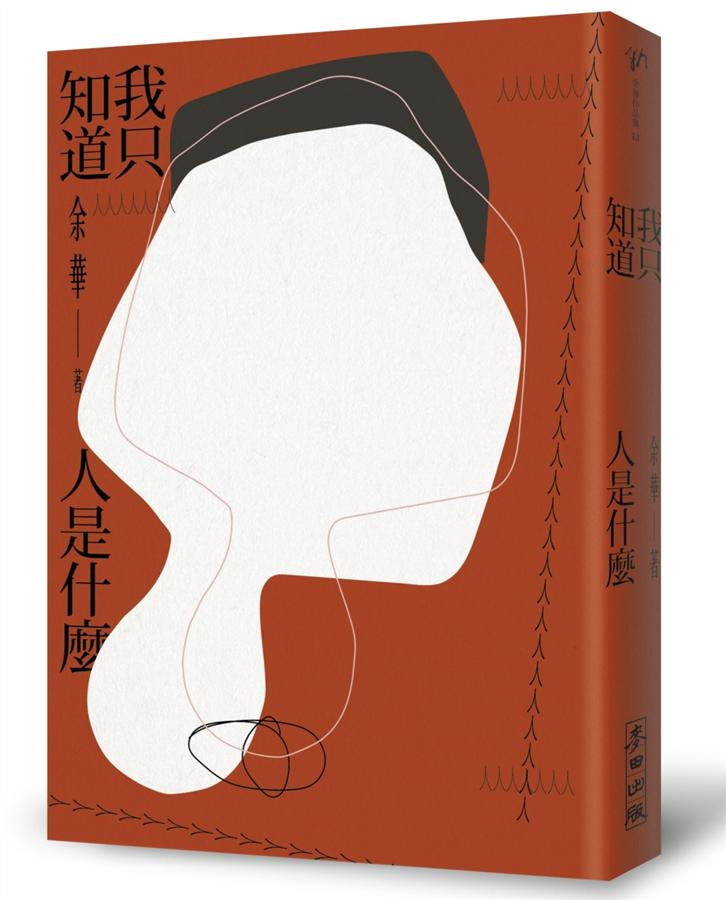
想要提升文字品質時,厚積薄發雖然偷機取巧,但卻往往有用。正因為深諳此道,每當有個主題想寫時,理想上會先看上三到五本書,再濃縮到一個相對短的篇幅之中,我腦補的畫面是,這能讓平淡的 Americano 變成香醇的 Expresso。
所以閱讀三本書再輸出一篇文章,幾乎成了我常見的套路;但只要稍加想想,就明白這做法是很可笑的。「著作等身」是個不合理的形容詞:假設一個人終其一生,產出了許許多多,卻都是垃圾,著作等十身也是搞笑;相反,以今天想要談的余華為例,當他三十一歲寫完《在細雨中呼喊》,三十二歲寫完《活著》,三十五歲寫完《許三觀賣血記》,四十六歲寫完《兄弟》之後,在我看來,就已經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在百年之後,那些作品依然會有人反覆地拿出來看。當然,一點都沒有嘲笑他矮的意思,我這矮不隆咚南方人是一點資格都沒有的。
好像有些扯遠,但我想表達的是,從碼字輸出的角度來說,若是沒有感覺,看了再多也盡量不要去寫;如果能帶給自己衝擊與力量,就算只是薄薄的一本書,還是要盡其可能的紀錄與表達,而《我只知道人是什麼》對我而言,就是這麼一本有力量的書。
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好句子像是在腦袋中無限冬眠的熊,鑽進去之後就不出來了;這句話就是我腦中其中一隻熊。聯想到老羅說過的一句話:「在一個國際主義者眼中,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狹隘的。所以當民族主義者們彼此叫囂誰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誰是不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時候,我們只能以同情的眼光打量他們。」
這兩句話基本定調了我的基本價值觀: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我對熱愛或厭惡一個過大的主體都不感興趣。群體是由個體組成的,但湧現的特徵皆是烏合之眾的,個體的複雜性不應該被淹沒在群體之下,1+1 與 2 本質上是兩回事,不存在大於小於或等於的可比較關係。身為個人能做到的只有,喜愛或厭惡一個個明確的個體。
藝術家經常會為神來之筆倍感驕傲,覺得自己有多麼了不起。當然他們有理由驕傲,但是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種恩賜,是對才華和辛勤創作的恩賜。
這種恩賜是對一位辛勤創作者最好的獎勵,是任何金錢與名譽都無法比擬的;先有對推敲的較真,賈島才對韓愈的一字指點感受強烈,微言妙趣往往產生於對一字一句的選擇與安排,你如果不曾身歷其境,便難免忽略過去,會錯過許多潛在的會心一笑。
我的演講題目叫《廣闊的文學》,這是兩個月前應主辦方的要求準備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當時選擇這個題目是基於自己的江湖經驗,演講的題目越大越好,題目大了怎麼說都不會跑題。
好的模稜兩可是一種藝術。古有《這一夜誰來說相聲》的「語言的藝術」,現有「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學習使用讓人無法反駁的、沒有建設性但也沒有攻擊性的、符合普世價值但也空洞的語言,似乎成為一種成熟與高情商的表現。而這好像有那裡不對,這種環境待久了,我會期待那種激烈的、極端的、衝突的對話。但扯遠了,這跟余華此處想講的沒有關係,只是很喜歡他這種自嘲的幽默感。
《兄弟》有五十多萬字,有時候寫著寫著就會犯錯,張清華就找到了一個毛病,小說裡面李光頭說林紅是他的夢中情人。張清華很溫和地問我,“文革”的時候會說這樣的話嗎?我說當然不會說,忘了嘛,寫著寫著就忘記了。張清華問我為什麼再版的時候不把它改一下呢?我說沒有必要,假如五十年之後這本書還有人讀的話,根本沒人知道“文革”時候的人不會說這樣的話的,今天在座的同學肯定也不知道那時候不會說這樣的話,如果五十年之後沒有人讀了,我改了也白改。
這跟我自己閱讀的體驗是很像的:長篇小說的許多細節的是記不住的,有時候整本書看完,我連主角的名字都記不得。我認為長篇小說看的是一種閱讀時的整體感受,是一種屬於過程的體驗,它更像是 Marvel 的英雄爽片,而非歐洲的獨立紀錄片。深度思考應當去找輕薄但高密度的哲學書籍,而別在長篇小說中尋覓那一兩句所謂的金句。
如何寫小說
威廉·福克納教會我對付心理描寫的一個絕招,簡單說就是當心理描寫必須出現時,就讓人物的心臟停止跳動,讓人物的眼睛睜開。
我的理解是,當細節足夠多的時候,量變會產生質變;涉及時間區間的細節是困難的,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四維空間,把時間暫停,抓出一個橫截面再去描繪是一種技巧。
但必須同時考慮文字的質感:短的描述往往是輕快而討喜的,例如:我在清邁天氣晴,且聽著風吟想著你。
相對的,冗長的文字天生帶一絲哀愁,適合偏憂慮一點的書寫,例如:坐在一個窗明几淨的角落,萬里無雲的天空,陽光毫無遮攔的撒落;古老且複雜的泰文、零散的斷壁殘垣、穿著樸實的當地居民,在清澈無比的眼神之中,透著不經意的呼愁,而這無來由的讓我想起了你。
當一部長篇小說是以對話來完成時,這樣的對話和其他以敘述為主的小說的對話是不一樣的,區別在於這樣的對話有雙重功能,一個是人物在發言,另一個是敘述在推進。所以寫對話的時候一定要有敘述中的節奏感和旋律感,如何讓對話部分和敘述部分融為一體,簡單地說就是如何讓對話成為敘述,又讓敘述成為對話。
這也說得太好!說書人是一個古老的職業,是小說家與編劇的祖師爺。區分一位說書人好壞的關鍵是節奏感。傳統上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現有韓劇強大的剪輯師,總能讓每集影集都恰巧結束在最扣人心弦的那環節。
什麼人說什麼話是寫小說的基本要素。
這是一個知易行難的要求。忘了那個作家說過,能產出好作品的作家,後設來看,都生活在某種程度的邊緣;唯有如此,方見人間冷暖,方有足夠的生活體驗與對話樣本,讓每個角色有合理的行為、用字、語氣,而這也是老表演藝術家口中的「真聽、真看、真感覺」。
首先要讓你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友誼來,你要坐下來,能夠長時間坐在那裡。
所以剛寫小說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寫,就拿起一本文學雜誌,打開來隨便找了一個短篇小說研究,什麼時候分行,什麼地方用什麼標點符號,我第一次學習的短篇小說分行很多,語言也比較簡潔,我就這樣學下來。剛開始很艱難,坐在書桌前的時候,腦子裡什麼都沒有,逼著自己寫下來,必須往下寫,這對任何一個想成為作家的人是第一個障礙。我要寫一萬字,還要寫得更長,而且要寫得有內容。好在寫作的過程對寫作者會有酬謝,我記得第一篇小說寫的烏七八糟,不知道要寫什麼,但是自我感覺裡面有幾句話寫得特別好——我竟然能寫出這麼牛的句子來,很得意,對自己有信心了,這就是寫作對我的酬謝。不過這篇小說沒有發表,手稿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外向活潑、擅社交的人能更好的體驗這世界;但往往是內心安靜、內向的,才是改變世界的那一票人。自閉 = 生產力。
八卦與趣事
我記得當時看過的一本外國小說,裡面有不少性描寫,我看的時候心驚肉跳,一邊看一邊觀察旁邊是否有人。
笑鼠我 xDDD 我也有過一模一樣的經歷:國小的時候看金庸,即使已經寫得比較隱晦了,但每當看到有男女角色在那個啥的時候,我都會默默地找到一個令人安心的角落再看 :)
繼續說《活著》。這部小說發表好幾年以後,我有時會想,當時怎麼就把第三人稱換成第一人稱了?可能就是一條路走不通了,換另一條路。我曾經覺得這只是寫作技巧的調整,後來意識到其實也是人生態度的調整。像福貴這樣的一生,從旁觀者的角度去看,除了苦難就沒有別的了,但是讓福貴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他苦難的生活裡充滿了歡樂,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們的家庭曾經是那麼的美好,雖然一個個先他而去。 《活著》告訴我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每個人的生活是屬於自己的感受,不是屬於別人的看法。
再強調一次: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屬於自己的感受,不是屬於別人的看法。這可能是過去一年最有感的體悟,有機會再展開來說。